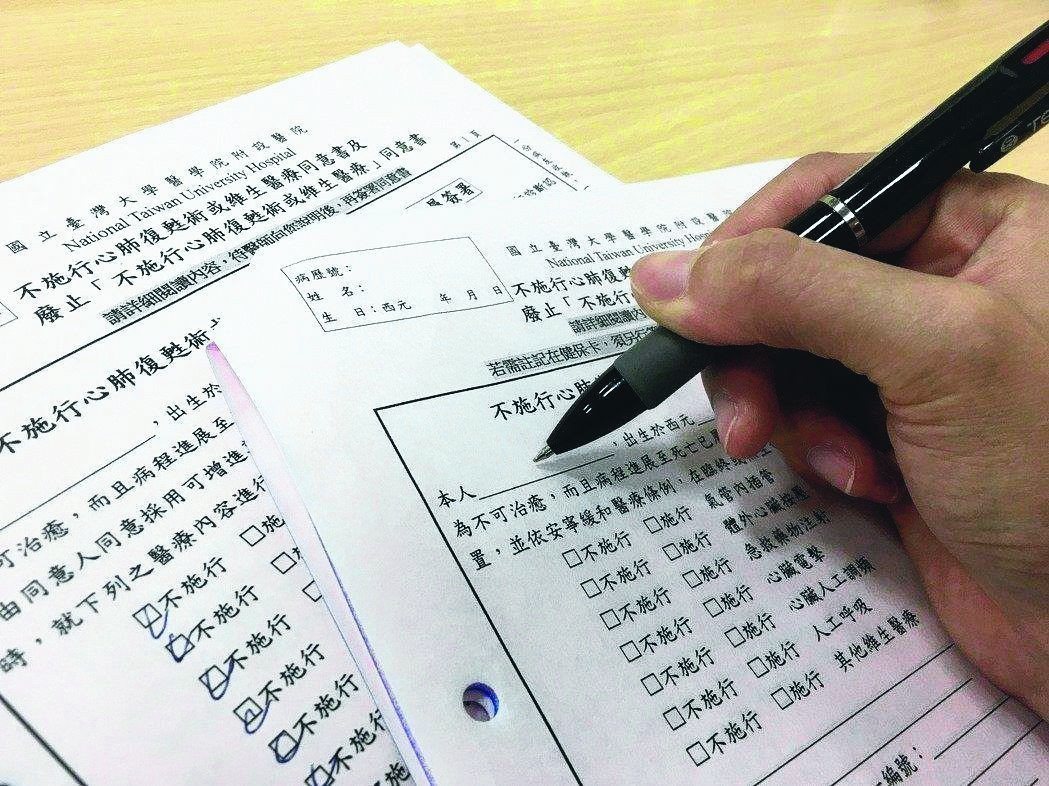2018-12-24 10:26聯合新聞網 文章提供/大塊文化
護理師喬照顧薩姆爾的時間最久。喬是兒科加護病房的助理護理師。薩姆爾因為院內感染,需要隔離照顧,最後幾個月都是喬在陪伴他。
喬一天有十二個半小時坐在薩姆爾和他母親身邊;晚上他母親到家屬休息室睡覺時,喬就獨自陪伴薩姆爾十二個半小時。我偶爾會去接替她,讓她歇一會兒,或是進去跟她確認藥物。
她若不是在對薩姆爾唱歌,就是握著他的手,或是撫摸他的頭髮。薩姆爾的眼睛跟著她在病房裡轉來轉去,彷彿在對她笑,實際上他應該很痛苦。喬在口袋裡放著泡泡水,輕輕在他頭上吹泡泡,然後把泡泡一個一個戳破,直到薩姆爾開心地踢腿。
醫生向他母親宣布噩耗時,喬陪在她身邊,即使已經下班,還是留下來把專業術語翻譯成簡單明瞭的話講給她聽。薩姆爾臨終之際,喬在他的手掌上塗了顏料,在卡片印下他的掌印,還從他後腦杓剪下一撮鬈髮給他母親。
這樣付出是一件危險的事,終究會承受不了悲傷,情緒崩潰。護理師承受的情緒太少獲得臨床上的督導,他們的所見所為也鮮少被探索,難以判斷他們的生活受到何種影響。
然而,好的護理師為了幫助病患,甘冒危險。喪禮過程中,喬傷心得直不起身。後來,我看見薩姆爾的母親走向她,兩人在教堂裡抱著彼此,空氣中瀰漫的悲傷籠罩著她們身旁的小棺材。
護理助產協會職業規範明訂:
二十.六:隨時跟你照顧的人、他們的家屬和照顧者,保持客觀、清楚的專業界線(包括過去你曾經照顧的人)。
只是好的護理師不可能永遠客觀。喬是個優秀的護理師,她知道照護人就是去愛人,即使病患已經過世。
 圖片來源/ingimage
圖片來源/ingimage
照顧病人生死的護理師
「遺體處理」也是護理師的工作之一。遺體護理,是你對另一個人能做的最親密的一件事。過程隱密,英國處理死亡的方式多半如此,而且也無法在教室真正學會。
我第一次看見屍體是在一般內科病房。當時我被分發到那裡受訓。跟我共事的護理師都是菸槍(有個懷孕肚子很大了,仍要出去哈菸),身上戴了太多首飾,頭上頂著失敗的髮型。
這裡的病人罹患各式各樣的內科疾病,如糖尿病、失智症、心臟衰竭、慢性肺病、腿潰瘍、髖骨斷裂,需要有人幫助他們飲食及如廁。工作項目重複性高。我們一一幫病患洗澡,不是看誰比較急著用便器,而是按照床號。一號床病患第一個洗,就算病患在睡覺也會被叫醒。
但今天什麼都往後延。病患在床上坐起來,因為不用被迫坐上椅子或在病房裡走來走去而一臉欣喜。
我走進病房時,有兩名護理師正在按摩一名死去病患的關節。我推著茶具走進去,推車搖搖晃晃,鏗鏘作響。我停下腳步瞪大雙眼,不自覺地張大嘴巴,直到名叫凱莉的護理師抬頭對我說:「親愛的,不要緊。他命很好,走得很安詳。家屬都來了。」
「對不起,」我說,拉著推車往後退。「我從沒看過。」
我慢慢後退,每退一步都差點彎腰鞠躬,總覺得有莊重肅穆的必要。我發現兩名護理師都在按摩他的手腳,好像他還活著似的,儘管他顯然走了。他的皮膚已經灰了,嘴巴開開的,看起來不像人。
「把推車擱在外面,來幫我們的忙。」凱莉說。
我想拒絕,找個藉口溜走,再也不要看見發灰的屍體,但我知道我要堅強。
我在門外先深呼吸再走進去,穿上圍裙,把推車留在外面。「妳可以從手肘開始。」凱莉說:「已經出現屍僵現象,但我們可以按摩讓它退掉。」
我有點噁心,猛吞口水,盡量不把眼前的男人想成一個人。這是我唯一能面對的方式:只想著他的手肘(現在變成味噌湯的顏色),輕輕按摩它,讓它不那麼僵硬:不那麼死板板。我盡量不去看他兒女的照片。還是孫子孫女?曾孫?
後來凱莉跟我解釋我們正在做的事:按摩出現屍僵現象的肌肉,再用枕頭撐起他的手臂。
「這樣他的手臂才不會失去血色或長出屍斑。」她說:「沒有什麼比屍斑更讓家屬傷心的。然後我們把他的假牙裝回去,用枕頭撐住他的下巴,接著為他擦洗。
稍微打扮一下,最後幫他貼上標籤,再用床單包起來。夏天就得這樣做。要是蒼蠅飛進鼻孔或嘴巴,遺體很快就會長蛆。再沒有什麼比這對家屬打擊更大。」
我目不轉睛盯著另一個懷孕的護理師。她喃喃說著:「是壽衣,不是床單。」我不敢問什麼是屍斑,努力想要趕走腦中屍體長蛆、自己死後蒼蠅鑽進體內、身體變得怵目驚心的畫面。
那天下午大概四點時,我趁著吃午餐到外面去走走。
「在想什麼?」跟我坐在同張公園長椅上的男人問我。
「生命與命運。」我說。
他哈哈笑。「聽起來好嚴肅。」他轉頭面對太陽,閉上眼睛。「多美好的一天。」
六歲女童的遺體
我旁邊是助理護理師莎薇。我們正在處理一個在祖父母家中池塘溺斃的六歲女童遺體。房間裡好亮,我們已經盡力拉上每扇窗戶的百葉窗。
房間沐浴在深黃色的光線中。躺在中間的女孩名叫芙蕾雅,在床上顯得好瘦小,頭仍躺在枕頭上,我們想盡辦法還是沒能讓她的眼睛完全闔上。我一直用指尖輕輕按住她的眼皮,為她闔上雙眼,但眼睛照樣彈開,彷彿從噩夢中驚醒。
死者的父母、祖父母和兩個兄姊(分別是八歲和十歲)決定不進來看我們進行的最後儀式。他們在病房入口旁的家屬休息室等候,我盡量不去想像他們在那個房間的情景:他們無法對彼此說的話,尤其是祖父母內心的自責。每個死亡都是一齣小悲劇,但芙蕾雅的死很殘酷。
她接了導尿管、氣管插管、中心靜脈導管、兩條周邊導管,還有兩支骨間針插在她的骨頭裡,此外,還有胸管和鼻胃管。「我們不可能把所有東西都拔出來。」我對莎薇說:「應該把東西都留在裡面,用塞子封住,再包起來。我會從她口中剪斷氣管插管,然後包住,這樣看起來就不會太糟。對家屬來說,這當然很難受。」
莎薇站在我後方,大房間裡已經沒有機器了,病床旁邊很空。「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屍體。」她說。
我深呼吸。我老是忘了這件事。年紀大了,從事護理工作多年,離年輕時的自己和豐沛的情感愈來愈遠,我納悶自己是不是還有那種感受。
除了家屬,醫院裡總有其他人為病患的死深受震撼:醫生、護理師、每天帶茶和點心來跟病患聊天的志工、協助病人看菜單的醫護助理、走進病房的理髮師、來檢查藥單順便小聊一下的藥局助理。但感受最強烈的往往是助理護理師。
資深護理師已經想辦法把心變成冰塊,以保護自己,但是要讓心變硬,得經過多年練習。我數不清自己看過多少遺體,太多了。
護理師很多時間都跟垂死的(昏昏沉沉、口齒不清)病患在一起,還有斷氣不久、還沒送進太平間、肺部仍有空氣的病患,病房裡仍充斥他們睡衣的氣味,彷彿聽得見他們的聲音。他們的微粒飄浮在空中,化為光線裡的灰塵。
「有時候說話會有幫助。我是說大聲說出來,」我對莎薇說:「當作這孩子還在這裡。」
莎薇從我後面走出來,淚水滿面。「可憐的一家人。」她說。
我搭著她的肩膀,輕輕抱住她。「哭沒關係的,其實哭很好,讓家屬知道妳真的在意。」我命令自己流眼淚,但淚水埋得太深。「哭吧。」我對自己乾巴巴的眼睛說:「哭吧!」
「在我的文化裡,為死者哭泣的時間是有限的。印度教認為應該為死者服十三天的喪。而且幫死者淨身的是家人,不是護理師。」
「這裡有時候也是。」我說:「但不是每次。最好問清楚,尊重家屬的意願。芙蕾雅的父母受到的打擊太大,連站起來都有困難……」我看著芙蕾雅。她的身體腫脹瘀青,皮膚發灰,被各種儀器覆蓋。
「開始吧。」我對莎薇說,然後轉向芙蕾雅:「小可愛,我們要幫妳小小梳洗一下。」
 圖/大塊文化提供
圖/大塊文化提供
我跟很多同事一樣,都會跟死者說話。這樣死者就不那麼像真的死去,護理師才能做好該做的工作,不至於傷心崩潰,或是感覺到死亡嚴酷的威脅。對死者說話,讓人感覺他們還活著。
人死去後,房裡會有一種氣息。若你有經驗就會知道,就像跟人爭辯之後、還有什麼飄浮在空中的感覺。
我認識的護理師多半都很務實,相信遺體就只是遺體而已。而我們不過是在空中飛舞的塵埃。不過每個護理師當然都有自己的鬼故事。